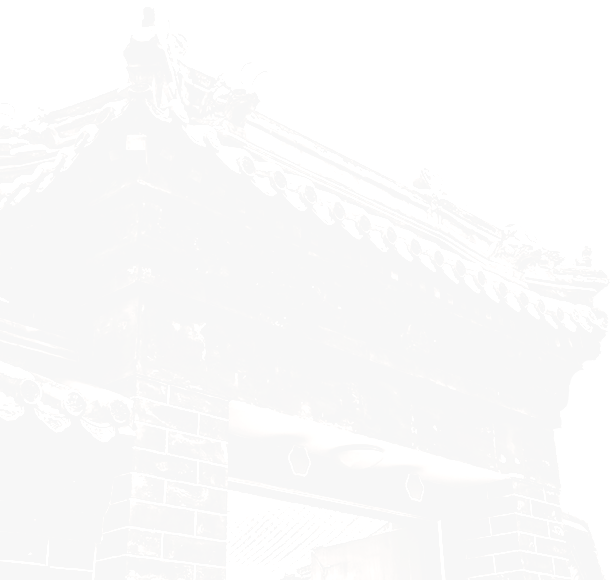亲历“肝癌”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吴天球先生在做肝癌手术两年后写的一万五千字的心得,讲述了其发病、手术、治疗的全过程,体现了一个笑对人生、坦然面对病痛、最终战胜疾病、重返舞台、继续参与社会音乐活动的积极精神。此文是一份可贵的人生感悟,令人震撼。主要内容曾在2008年新学年伊始的支部大会上口述过,趁此出刊之际,刊登此文,使之传播得更为深广。
由于篇幅有限,刊登时对文中一些有关医学上专业名词术语的解释、诊疗过程做了某些删节,特此说明。
* * * * *
文艺工作者提倡体验生活。体验的范围非常广,可说是应有尽有,皆可提倡体验一下。但恐怕没有人想到需要体验患“癌病”的经历,要去经历“手术”、“化疗”等等吧!
我却意想不到地亲历、体验了一场。人们一般不愿谈及这种事,以为不吉利、不愉快,而我却想把它写出来供朋友、同行们作为间接体验,大致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或许必要?
序幕
2001年3月某日,2023澳门原料网大全退休办组织离、退教工到北大医院进行体检,我也参加其中。在进行腹腔B超时,在场的医生们反反复复,费时很长,神情紧张,多次问我:“你有什么不舒服?”我回答:“没有!” 我反问:“有问题吧?”医生说:“有点问题,你应该尽快到医院门诊作仔细检查!”我笑笑回答:“好吧!”
约过一周时间,退休办让我去拿体检结果,并要我尽快到医院仔细捡查。我仔细看了体检结果,在B超一栏内写着:肝部有一个直径为3.8公分的低回声团(即肿瘤)。为遵医嘱,我到我大儿子工作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进行CT及各种血象检查。CT查完,具体操作的医生对我儿子讲:看来是恶性肿瘤,这可吓坏了我的儿子。但是,放射科主任仔细看各种检查结果后说:不像是恶性肿瘤,而像是“肝岛”(脂肪肝造成的一种肿物),并出具了检查报告。随着,我将所有检查结果带到北大医院挂放射科的专家号,请北大医院的放射科主任诊断,该主任说:“这些片子拍的很仔细、很清楚,下了很大功夫。我同意广安门医院的看法,不像是恶性肿瘤。”主任也出具了诊断报告。这样,我照样乐呵呵地过日子。
2002年、2003年、2004年的每年3月学校照例组织到北大医院体检,我都照例参加,每到B超室检查时,大夫们照样神情紧张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我照样回答“没有不舒服”,我进一步问:“是不是有一肿块?”“有多大?”大夫回答:“是有肿块,有4.5公分,你也知道吗?” 这是2002年的情况,之后,2003、2004,肿块递增至6.8公分、8.7公分。体检大夫一年比一年紧张,退休办一年一年摧我检查,我反倒越来越无所谓。
2005年3月又照例体检,又到B超室,大夫很严肃地说:“你这一肿块己长到10公分左右,再不及早治疗将很危险了!”于是,我脑子里想:“它还真长得快呀!”这才开始比较重视。
当时我和老伴巳报名参加旅游团赴欧洲玩半个月,心想:假如是良性的等欧洲回来再处理也来得及;假如是恶性的,更要坚决再去玩一趟,否则今后就没机会了。全家统一此认识,将检查看病的事不管了。5月初,老俩口相伴游欧洲,5月中老俩口尽兴而归。
5月底,我又到广安门医院做CT检查,主任说:“看样子仍然是良性的,但长得太大了,最好是拿掉它,以防恶变。”我带着CT片请教几家医院的几位主任医师,多数医生也认为是良性的,但长得太快、太大,应该手术拿掉。综合多数医生的意见,家庭会议决定:“拿掉它!”我把这次手术定名为《剖腹产》。
于是,我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门诊部观看各科医生的介绍牌,在腹外科选择了一位中年的男主任医师作为我的主刀医师。我们的依据是:中年主任医师身体好、精力充沛、有开创性、技术先进。我老伴说:“这动刀动枪的事,还是中年的男人有把握”。
选择已定,我就去挂这位专家号。他笑着说:你怎么把它养得这么大?就算是良性的,它要是破了也会要你的命!我笑着回答:这要命的事只是早、晚的问题。他让我立即在6月份住院手术。我因教育部7月20日有一比赛请我当评委,故请假到7月底住院。医生一歪头说:长年已过,何在乎这一个月!
7月22日,医院有床位,老伴帮我拿一些用品乘出租车到医院办理住院手续。25、26日进行术前检查,手术确定在2005年7月27日上午8时进行。
术前检查是复杂的事——CT、B超、验血等,虽折腾人、烦人,但这些都是将自己交由医生操作就行了。而另外要同时进行的术前准备则需要自已很好配合、懂得配合才能顺利进行,才能减少痛苦的,如锁穿、灌肠、插胃管等。
手 术
7月27日清早,我很好地洗了澡,换好干净衣服,然后呆在病房静待手术室推耒运送病人的病床接我。7点半正,只见一位工作人员手拿病历卡,看着病历叫:“吴天球有吗?”我回答:“我就是!”, 边回答边走出病房 ,从容地到手推病床上乖乖躺下。工作人员为我盖了一条白色被单,一顶绿色纸帽戴在我头上,由于我头太大他戴得相当费事,我只得自己动手戴上。
当天我老伴和两个儿子都来守候,他们静静地守在我身旁,神情严峻,见我在笑他们也只好跟着“苦”笑!陪我从电梯上搂,出电梯,走到手术室门口,有如上飞机过关一样,到了这个门口,我将被推进去,他们只能留在门外等。
通称的手术室原来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有如一个大礼堂,中间有一条宽长的走廊,两边才是一间一间的真正的手术室。我被推进去后就先在大走廊停住,一张床挨着一张床排好队。我似乎是第五、六个到的。约半小时内很快就进来许多病床,将整条走廊都排满了。在一片寂静中连呼吸都听得见,还能听到轻微、有控制的咳嗽声,隐约有一、两位女声的抽泣,其声发闷,显然是用被单捂着嘴在抽泣的。这时我想起歌剧《伤逝》中的咏叹调“不幸的人生”中的第一句歌词:“又是死一般的寂静,又……”。我躺着转头向左右看,只见平整的病床上盖着一条条凸起的白床单,我想数一数有多少床,但水平角度无法看清楚,我注意到护士不在,索性坐起来仔细地数了两遍,哦!有十九个床了!这时突然有一位护士出现了,她发现了“情况”,立即悄悄地快速地奔过来,到我跟前严励地压低声音问我:你怎么了?我头、手并摇笑笑地用“气声”悄悄回答:“没事!”同时赶紧躺下理好被单,一动不敢动。护士奇怪地瞪我一会儿,不解地走开了。这时又有病床推进,我再不敢坐起来数了,以免护士受惊吓。
我躺在手术台上,第一位接待我的是年轻的“麻醉医生”,他告诉我:他也在福建当过几年兵,会听几句闽南话。他进一步为我“备皮”即在肚皮上擦洗、消毒、刮汗毛等。一切做完,只见他用针管在抽一种药水,要注进我的输液袋中,我问:你现在要给我打迷魂药了,让我迷糊之后,好把我的“心肝宝贝”偷走是吗?他稍一楞神,说:哼!是这样。之后,我果然一无所知了!
等我苏醒时是在我的病房里,只看见医生、护士、我的老伴,两个儿子等好几人,几个男的很费劲地要将我这大胖子从担架床上往我病床上移过去,真难为他们了!移毕,我见他们都围着看,都站着,出于礼貌,我术后的第一句话:“都请坐吧!”我那当医生的大儿子说:你现在还要管我们哪?我无言以对。又听到呤,呤声,我提醒他们说:有电话!大家都笑了,原来是监测我的仪器在响,这还是出院后,老伴在聊天时说的,否则我还不知大家在笑什么?这时只见我的右侧有一中年女子,边为我压被子,边说:“叔叔,你不用管了!”我问:你就是来照顾我的吗?她点头,我老伴说:“是!”于是,我便在这位小刘的精心护理下,进入术后恢复期。
现在需要着重补充我被麻醉之后到我清醒之前这一段我被全麻时间内的情况。
先说一点麻醉的常识。只要是动手术的治疗,通常都要麻醉,轻的局麻,重的全麻。局麻时病人神志清醒,手术后麻药自动逐渐消失,麻醉不存在太多风险。全麻则是针对中枢神经,它让病人全然不知,在麻醉起作用阶段,病人如死去一般任由宰割而不知疼痛更不知害怕。这种麻醉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讲究的是个“度”和“时”的把握。度:麻药给少了,麻醉度浅,病人一挨刀疼醒了!这当然不行。更可怕的是:麻药给多了,麻醉度太重,伤了中枢神经甚至病人再也醒不了啦!时:就是病人该什么时候失去知觉,到时就得不省人事,以便按时做手术。更主要是讲究病人刚回病房就按时醒来,若早醒,病人还在手术室或在路上,这对刚术后的病人不利。要是回到病房,躺上病床仍然没醒,这对病人有害。这让人担心病人“醒得了吗?”就是能醒,延长麻醉时间对病人也是伤害。这麻醉的学问大啦!我只略知这一点点,还不一定对呢!写到此,再想想我刚回病房就能醒过来,而且有一定的思维,还能说出一些不合实情的傻话,这对一位刚被重度麻醉近五个钟头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当时说出的话虽可笑,但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我的手术进行了4个半小时,从白刀子进是上午9点直到红刀子出是中午1点半,这是刀光血影,开膛挖肝的4个半小时。在这期间,老伴和两个儿子在手术室外的一间大房间里等待,要随时听手术室里面的呼叫,例如:某某家属过来!家属就得到玻璃墙的窗口,医生就对他讲手术现场的情况。最怕听到的是打开后发现已转移或其他情况而不能切除,必须原样缝合,家属同意,签字。更怕听到的是:病人因出现意外而死亡,家属认可,签字等等。我大儿子是医生,总给病人开刀,这一点他早巳熟知,但他这次不是以医生的心情来坐在这里,而是和大多数家属一样忐忑不安地等待对我的宣判。我老伴的心情肯定更复杂,不过据她讲:我认为你绝没事,所以不紧张。也“真”刚强?!1点半时,里面叫“吴天球家属过来!”他们三个一起到窗口,只见主刀的主任医生手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颗大大的,红喷喷,亮光光的内脏切除下来的瘤体。主任说:手术顺利,非常成功,我看是腺瘤,当然要等病理切片后再确定。三位家属自然很高兴,悬着的心放下了!
介绍一下这个瘤体:直径15公分,重1050克,由于瘤体太大,所以我的肚皮上的刀口长28公分。瘤体的包膜完整没有扩散转移。后来病理科发来通知:瘤体的中心有癌细胞,所以定性是:恶性肿瘤!医生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大肿瘤,因此在我即将出院时,医生找我说:你的那颗肿瘤太大了,我们要留下做研究用,你如果同意请签字。我回答:这个东西我拿回去也不能炖着吃,只要满足我一个条件你们就可以留下。“你讲”医生说。我说:我这个心肝宝贝什么样,我始终没看见,能不能照一张照片给我让我也好看一看。医生说:没问题!一直等到我出院回家,我用Email提醒医生,果然在电脑上传来这颗肿瘤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顶部和四周光亮鲜红,底部是不规则的切面,非常好看!另一张是中间被切开,尚有一部份包膜连在一起,两个刀切面展开照的,能很清楚地看见肿瘤的外面有一层约一毫米的胶状外膜,而里面,噢!那简直是一包乱七八糟的黑色小物体,极度难看,我也看不懂,当然,我知道这些黑点的中间就有“万恶的癌细胞”。
手术完的前几天必须绝对卧床,一切的生命必需都靠各种管子输入和排出。这时身上的管线有:输液管、引流管、倒尿管、胃管、吸氧罩五条管子就联结在身上的上、下、左、右。想想真好玩,别人看了真“恐怖!”。在我拔完这些管子能上走廊学走路时,有一位也刚出来学走路的病友,关切地问我:“你身上也插了许多管子吗?”我说:是的。他说:“哎啊!我也插了好几条,真难受死了!”我说:“还好吧!这也体验一下生活!”他猛一楞、惊奇地瞪着我,再不跟我聊了!这些管子在手术之后的五天左右就先后拔除掉。
照说,这样大的手术,这样又大又多的伤口,在麻醉过后一定会很疼的,但却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这要归功于神奇的“止痛贴”。原来,在我的左锁骨下方贴了两张的“止痛贴”,它像“伤湿止痛膏”一样,只贴在皮肤表面,没有任何不适。据后来有大夫介绍,这药膏的成份是“杜冷丁”,渗入皮下起止痛的作用。这药膏的效力是三天,而三天后取走膏药,伤口也不太疼了!真好啊!
术后
术后四天,先后拔完了我身上的管子,(输液底座还留着,在需要输液时可随时接上,不输液时我可带着它下床。)我就可以坐起来,下床学步了!可以上厕所了。有可能排出后就必须要先进流食,才有废物可排,并可以逐渐减少通过输液管输入那些维持生命的液体。一听说可以吃东西了,真高兴!五、六天饿肚子的感觉可以结束了!
早晨,老伴专门为我做的一碗香喷喷的米汤端来了,先喝一小口,淡而无味的米汤此时喝起来也觉得滑润、喷香,接着我就正常地喝一口,刚咽过喉就梗住了,通不下去,憋得我喘不过气来,脸色青紫,喉中吁吁作响,脖子一伸一伸地抽动。吓得我老伴和护工小刘一大跳,她们在我前胸、后背一阵轻拍、慢揉,约十分钟才算通下去,才能正常地吸气,脸色也才逐渐恢复正常。之后,我就一小小口地慢慢喝,用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喝完。我事后想:这咽管、食道、胃肠等,好几天不用了,定然狭窄,功能退化,不可能一下子负担起正常的吃喝任务。当时真让人吓一跳,事后又觉得好笑,我与老伴每谈起这一段,总觉得不可思议而笑起来。如果当时出事,说出来是:“吴天球让一口米汤给咽死了!”多可笑啊!
住院巳经七、八天了,手术后也有四天了,我同房的病友每天都要接待一、两批的探视人员,他是河北人,每批探视的人员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都是他的亲友、同事、包括他的儿子们的同事和朋友,开着专车进京,一堆礼品几个花篮,摆满屋。显然这位老兄在当地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他儿子也是一名领导,这领导得了癌症做手术,或领导的父亲得了癌症动手术,这要来探访的人那是排不上队了!每次来人探视,他的三个儿女都忙着接待,这老兄也得对人表示客气,讲话就多,显得很累!而且这些探视的人一走,所有鲜花也立即清出病房,医生说:病房摆鲜花空气不好,又显乱,所以可怜美丽的鲜花随着送花人的离去也惨遭遗弃。
与这老兄相比较,我是十分清静。住院前我就与老伴商量,我的这次住院要绝对保密,不是因为得癌症不好意思说,而是不愿意使亲友们冒着酷暑到医院探访,我也免得因接待亲友而受累。若有人问起我,就说:“他回厦门老家了!”回老家是很正常,无需理由的。就这样,连我老伴的姐姐也没告知,我很安静、安心地养病。我的病床旁最多两个人,一位护工,一位家属。家属即:老伴、两个儿子。他们三人分头轮流来陪我,主要目的是替换下护工回去睡一个好觉,以免她太辛苦了。想起他们三个人来陪护,三个人三个身份,很有趣:
老伴:她一来总带点吃的。当时我若躺床,她坐椅子,我若是坐椅子,她也会叫我躺床她坐椅子,有时她陪我走走。
大儿子:他一进来,挺胸昂头问:怎么样?知没事,说:好!然后就站着,椅子空在那里他也不坐。叫他坐他摇头,他说医生在病房绝不许坐!噢!原来他不把我当爹看,而是当病人,他是来查病房的大夫啊!
小儿子:摇晃着进来,“老爸!没事吧?”“没事!”哈!哈!哈!东翻翻西找找,见吃的塞嘴里。摸摸床,“嗨!这床顶舒服的。”我如坐椅子上,他脱了凉鞋就上床躺下!翘上腿摇晃脚,不着边地跟我聊,聊聊聊,他睡着了!我拉近椅子用报纸轻轻为他扇风!噢!原来他不把我当病人,而只当老爸,他是来老爸怀里休息的。
约术后一周,我老伴来电话对我说:有一位李宁光打电话来约我9月30日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我说不要回掉,让我想想。“想!”想什么?第一、我身体情况:一周来我康复很快,已可以挺直身体到走廊漫步十几分钟,吃饭开始正常,我在光依靠输液维持生命时,我的体重就比原来有增加,现在吃东西了,动起来了,体力精神都比较好。第二、应是我担心的:我的嗓音会不会有变化?我用说话的声音试试,故意用大一点的声音,带有共鸣的感觉讲几句,嗯!没有变化!我很高兴我的嗓音还在!第三、最担心的是:我的大肚皮有一条28公分长的垂直刀口,在当时,这刀口还用“钉书钉”钉着,还没有拔钉子呢?如果唱歌时用气,伤口会不会崩裂,或是说会不会很疼?办法就是“试!”,我走进厕所适度地练唱几声,我发现我的伤口并不疼。原来,歌唱时的用气,其张力在后腰而不是在前面的肚皮上,这倒是让我对歌唱用气的原理有新的体会,太高兴了!既然在刚术后七天,钉子还没拔都不疼,两个月后肯定没事的。我决定答应参加9月30日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唱。这一决定对当时的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必须请示医生。第二天早上8点主任查房,一大帮医生也都跟着,查完病情我站起来说:我有一件事向主任请示。主任说:请讲。我就将决定参加演唱的事说了,当时大家楞住了,任何人从来不会想到刚术后七天的大病号会提出这种问题!沉默间,我进一步向他们解释,我介绍了我的恢复状况、嗓音状况、歌唱用气状况,并当场发声证实,之后我说:我觉得我还行!主任说:你本来就行!当时他伸出手指一算,说:、“嗯!到9月30日两个月,可以!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急,要恢复一段再唱。”我说:“我8月份一声不练,9月份开始恢复练习。”主任说:“好!”我说:“到时我请你们光临音乐会,一表示我的感谢!二向你们汇报,三请你们验收,看看!你们不仅挽救我的生理生命,而且还保留、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大家很高兴说:“我们到时一定到!”主任与我击掌告别!当天我就告知李宁光确定我参加演出,并报上五首演唱曲目。仍不说做手术的事,免他担心。
出院
8月7日予告我可以在8月10日出院,所以要做第一次的拔钉子,拔钉子有专门的工具,插进钉子下面用手一握紧,钉子从中间压下两端翘起,钉子就出来了,小钉子口会渗出一点点血,酒精棉一擦就好了。为保险,第一次是两个拔一个,即隔一个一拔,留下另一半,以防一下全拔光时伤口尚没有粘结实造成大崩裂。另一半到8月9日才拔,观察一天没事,10日才平安出院。
出院前,主任医生找我和老伴谈话,交待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其中一条是复查:头两年是每三个月来院查一次,项目是:CT、B超、胸片、血象。第二,主任说:由于肿瘤的中心已有细胞癌变,但包膜完整没有扩散,一般人也就没事了,但对于你,我以为还是做一次预防性的介入(即化疗)好些。就做这一次。主任的关爱、负责、诚恳,令我感动。我说:“好!什么时候做?”主任说:“最好出院休息两周就来做。”我说:“化疗对身体的损伤更大,我9月30日要演出,可否等演完了再来化疗?”主任说:“对啦!演出前不能做,演完了再来。”我提出:这9月30日演出完,紧接着十一黄金周,我只能在10月8日住进来。主任同意。我要求事先开好住院通知单,这样在9月底我就可以在学校办好住院的押金支票及向医院预约病床,以便10月8日准时无误地住院。主任欣然同意!一切办得愉快、圆满,准备在8月10日出院。
8月10日一大早老伴为我带来了家中日常穿的衣服,我也一早起来梳洗、整理,换下紧身的住院服,穿上自已宽大合适的服装,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显精神,像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一样的高兴!我早早地等待着出院,我穿着自已的服装在病房内坐着,上走廊走走,病友们一见都知道我要出院了,送来了祝福的眼神和友善的问候!我很高兴地、由衷地向医生、护士一一地表示感谢和告别。11点多钟办完出院手续,小儿子用车来接我,我最后向日夜照顾我的护工小刘告别并表示十分的感谢,她实在对我照顾的太好太周到了,我康复的快与她的很好护理有直接的关系。终于我很生疏地坐进小车,很感兴趣地观赏本来早己熟悉的一路的车流和两旁的楼宇,这种新鲜感说来也奇怪!
回到家,家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总很新鲜,十几天来医院给我的印象太强烈、太深刻了!在沙发上略坐片刻,老伴扶我进屋躺床上,一看,老伴己把房间和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床单、被套都新换过的,原本这些是平常的事,这时对于我却十分有感染作用!不料,就在我刚回家,刚躺床后就出了一件危险又可笑的大事故:我太胖,肚子太大,这28公分长的大刀口垂直在中间,仰卧时刀口在中间朝上,侧躺时这大肚子就会住床板上坠下去,对刀口起一种拽裂的作用,刀口就很疼。我在医院时病床边上总放着一个垫子,在我侧躺时垫在肚子的下面,把肚子托住,这样肚子就坠不下去,刀口就没有撕裂的疼痛感。当我躺到家里的床上后,自然会左右翻转试试,发现没有“肚子垫”,我就对老伴说:你帮我找一个乔麦皮的枕头。她问:干什么用?我把用处一说,她乐了!说:有!立即她就找来了一个约六、七斤重的乔麦皮枕头,离我还有二、三步远就笑呵呵地说:给你!同时,这沉重的枕头己砸到我的大肚子上,当时,我大声惨叫!她这才清醒过来,抱歉地说:哎哟!我忘了你是病人啦!我在疼痛中接受她的抱歉,因为“忘了”犯下的“错误”,上帝也必须原谅的,幸好肚皮的刀口没因挨砸而破裂,疼一阵就过去了!至今我们还常常谈起这件事而觉得可乐!这件事很典型地表现出我老伴的性格、特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回家第二天,我带着“出院报告”及一应手续,特别是那张不能折叠的《支票》,此支票是住院押金在扣除住院费用后所剩的一小部份,必需在五天之内交到财务处,否则过期作废。我带着这些材料先到校园东侧的医务室找主管核签的大夫,因材料太多特别是那份“明细表”,一样样的审核,再一张张的签字盖章,所以花了近一小时。之后我再“漫步”到学校的西侧办公楼二楼,进财务处办理。接待我的女士仔细看了支票完整无损,将支票收下,再看医院的出院报告写着“肝癌手术”吓一跳,她抬头看我,见我笑咪咪地看她,又看看名字是吴天球,她本是学校的老同事,对我很熟,以前我去报销,她一听声就知是我,报销快速顺利。今天她用迷惑的眼神盯住我问:“吴老师您这是给谁报销呢?”我说:“我呀!这名字不写得很清楚吗?”她:“哼!不像!”我笑了:你不信呀!她还是看着我摇头!当时是8月上旬天气热,我只穿了一件带领子且领口有三个扣子的T恤衫,我灵机一动,就解开领口的扣子拉开领口,从柜台外抬头向内倾斜说:你看看吧!这位可爱的女士从椅子上站起来,垫着脚尖伸着头从柜台内向我的领口的空洞窥视,她终于看见了我肚皮上半部的伤口,于是皱着眉头说:哎哟!还真是你呀!我说:既然己“验明正身”就可以报了吧!她边办边还念叨:“不像!不像!你怎么就自己来了呢?刚出院不是!”在摇头中她办完了!
8月份在家休养,开始只在家中走一走,坐一坐,时常躺一躺。后来可以下楼到学校附近的小绿地散散步。练声、唱歌的事一点都不做。到了9月1日我开始打开钢琴练唱,先轻声在中低声区活动嗓子,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三、四天后声音逐渐放大,时间逐渐延长,半个月后开始与老伴和钢琴伴奏,也是先轻声找感觉,然后再逐步放大,逐步按要求练习。到9月20日我已能自如地歌唱,对9月30日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唱充满信心!9月30日我邀请了肿瘤医院的许多大夫光临音乐会,主要成员是蔡建强主任医生的医疗小组,他们听后很高兴、很惊奇!说:你是我们亲自为你做手术,最了解你的病情和伤口情况的,否则从今天台上的演唱完全不能相信你是两个月前刚动了大手术的“人”!我!总算闯过了“生死关”“演唱关”,能像健康人一样站立舞台、放声歌唱!我!内心非常激动!
化疗
演出结束,在家过“十一黄金周”,10月8日我按出院前与蔡建强教授的约定,又一次住进肿瘤医院的介入科(即化疗科)。日程是:8日住院,9日作化验等等,10日手术,13日出院。非常快速,顺利!这里有必要稍加介绍:
手术:经过大开膛的锻练,对这一手术我根本不在话下,可我那当医生的大儿子却很重视。这一手术就是将右大腿根处的主动脉切开一个2毫米的口子,插进一根粗的导管,里面再套一根输药液的细管,顺着动脉血管一直通到肝脏,这导管的头勾住肝脏的主要血管,连接好后就将药液(毒药)输进肝脏,等整个肝脏灌满毒药之后,再将这两根导管撤出来。由于这个口子有2毫米大,又是直接进主动脉,所以要用一块近半寸厚的纱布使劲按压四小时(我实际按压了八小时),否则可能造成血喷。当时我并不懂,推我进手术室,这间手术室似乎是介入科自已的手术室,是个套间,外间是机房,内间是病床和一台输液的机器。医生看我一点没事,就跟我聊天,我在输毒药时他们还在问我如何唱歌?聊着聊着15分钟输完了,从里间推到外间时,我正在向他们示范“发声方法”,我躺床上就唱开了:1-3-5-3-1,用啊母音唱的。高高兴兴我被推出手术室,我还在笑,我儿子就吼我了:“你干嘛啦!”我问:“怎么啦?”“你在里面大声唱什么?你知道有多危险?万一血喷出来就能直接喷上房顶,止不住的你知道吗?”我小声地说:“不知道!”再不敢吭声了,心里想“小题大做!”
回到病房,赶上开饭,我照吃不误,同房病友问:你没感到恶心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有的人在手术室输荮时就吐了。噢!怪不得我看见有人在等候手术时准备了两个塑料袋,当时我还觉得奇怪!这干嘛用呀?当晚护士来测体温、血压等等,我全都正常。
第二天(11日),主任医生带一帮人来查房,一看病历样样正常,一问病情没有异样,主任说:很好!我笑笑地问:“大夫,昨天给我打的药是不是打错了?”大夫一楞!紧张地问:“怎么啦?”我笑着说:“是不是打了开胃药?所以我吃嘛嘛香。”大夫狠狠瞪了我一眼,一句话不说领着大家走了。第三天(12日)上午,又到查房时间,只听走廊上有大夫、护士的走动声音,我立即规矩地躺着等待查房,又过了一会儿,我的护工小刘走过来说:“叔叔!刚才主任带一帮人走到咱病房门口,突然停住说:‘他(指我)什么事也没有,不用看了,让他明天回家吧!’说完就进别的病房了!怎么办呢?”我哈哈一笑:小刘呀!说明你把我照顾好啦!大夫省事啦!于是我打电话让家里准备接我回家。第四天我就出院了。在走出病房楼时正碰上参与把我大开膛的一位大夫,知我化疗出院很高兴,但他关切地提醒:“化疗后的反应要过几天才慢慢表现出来,你要注意!”我很感谢,当时也很不理解。
回到家开头几天我一切正常,吃饭正常,也不掉头发,但总觉得肝区有不舒服。过了一周后开始掉头发,一洗澡掉得更多了,一把一把的抓在手里,本来我的头发是比较多的,但在两个月之内掉得很稀松了,头皮开始外露了!更主要是体力差,很累,怕冷,别人穿毛衣我要穿棉袄。脸色越来越青灰色,嘴唇暗灰色,脸上、身上莫名其妙地长疙瘩,牙齿松动腐朽崩裂。但可喜的是我始终保持好的胃口,声音没有变化仍可歌唱。我在刚化疗后的几天内,1.接到教育部邀请在11月初到南宁当评委的任务。2.接到11月25日在广州中山堂演出消息。3.接到11月26日在我家乡厦门参加《世界同安联谊会》并在开幕式上演唱活动,我全答应了,并且都顺利完成了。这全得益于我的好胃口和嗓音没变这两点。在外面别人只看出我行动迟缓,这都可以搪塞给“太胖了!”此外在精神情绪、嗓音及演唱效果都很正常,谁也看不出我得了可怕的“肝癌”而且刚开完刀,刚进行化疗!
过了将近一年,肝区不适逐渐缓解,长出来的毒疙瘩慢慢脱落,脸色青灰开始变红一些,牙齿不再继续脱落。特别可喜的是:头发不仅不再脱落,而且逐渐又长出来,甚至比原来还多,更不可思议的是竞然弯曲成波浪形,随便一梳理便很好看。我老伴时常用羡慕的眼光夸我头发真帅,我则劝她:别再烫头发了,越烫发,头发越少而且还花不少钱,不如我带你去化疗,将来头发长得更多还自然弯曲,比烫出来的好看,而且不仅可以省下烫发的钱,化疗的钱还可报销!多好!她不语!至今她还没转过“这个弯”来!遗憾呀!哈!哈!
手术至今(2007年底)己近两年半,头两年我坚持每三个月复查一次,结果都基本没问题。在2007年7月我再复查时,蔡健强教授说:两年了要好好查一查。查的结果仍然没扩散、转移、复发等问题。按当时出院时的医嘱是第二个两年内应半年查一次,但蔡教授说:一年一查就行了!这等于是直接跳级到第三个两年时段的检查规定。这能说明什么?不好解释!反正高高兴兴听医生安排。
这两年多时间,凡有邀请我参加的活动——演唱、评委、讲学、旅游、渡假等,我都答应参加,也都顺利完成,没有因身体因素而推辞,也没因身体因素而有所降低质量。
感悟
当化疗后体质下降时,我很理性地判断自己的生命己进入“倒计时”阶段,可能还有十几年,也可能早、晚随时发生。所以我萌生了要在我好心情、好精力的情况下,把自巳长久以来对身后事的一些理解整理出来、安排交待清楚,以免到临终时己没有精力和理性,什么也说不清楚,说了家属也没心思听。于是在2005年10月,我一边准备赴广州、厦门的演出,一边写我的“留言”。由于“留言”中的内容己经想了多年,而且这些想法也早就和老伴交谈并取得共识了,所以写起来也很快。我想不妨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也是我对“肝癌”、对人生的感悟!
在我手术后,我与老伴常就“我死之后”为话题闲聊,基本内容:丧事不办、骨灰不留、不及时通报亲友、不改变家里摆放、不戴孝、不哭泣、不请假。有如我回厦门老家一样。两人边谈边笑,氛围很好。举一例:关于遗像,老伴提议挂那一张好,我就同意,理由是反正是挂给他们看与我无关了!但我坚持在像前一定要摆假花,不能摆真花。原因是:1.真花污染。2.真花容易雕谢!3.真花常要换水。老伴糊涂绝对不记得换水,两天后水就臭了!她听明白了,也知道自己粗心,就同意只摆假花!过一段,我感到目前家中所挂的像相当喜庆,所以提出家中不挂遗像,理由是:不要让人一进这屋就像走进灵堂一样压抑,不要提醒客人这家死过人,更不要让家里人随时看见遗像随时想起这死去了的我!我们交谈这些非常坦然,高高兴兴,我想这是最好的“思想准备”。‘到那时’我相信我的老伴不需要什么劝慰,因为我们早己谈透了。
通过谈生、谈死,老伴有一大进步,虚心多了!以前家中有些小活她其实也能干,学一下就行了,她偏不听、不学,反正有你来干就得了,我学它干嘛?这会儿不同了,我说:“你要学了,不然我死了你怎么办?”她也明白了,就耐心听、虚心学,态度好多了。
亲历“肝癌”就写到此。我觉得:人得病是自然的,老人得病更是必然,进一步说,老人得病后死亡也是必然的,不用怕也不用愁,怕与愁并不能减轻病痛,反而增加了怕与愁给身体和精神带来的伤害。而且病人自己的怕与愁,痛苦不堪的样子,将极大地增加亲属们的痛苦和精神负担。病人心情好,时常笑一笑,既可转移对病痛的感受,更可极大地缓解亲属们的痛苦和负担。这也是我亲历“肝癌”后的一点收获!
吴天球
2007年12月